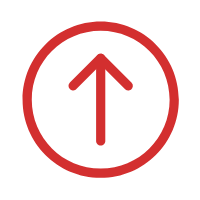作者:创文文
简介:主角是林夏阿芸的叫做《霓虹账本跨世的数字绳结》,这本的作者是创文文倾心创作的一本豪门总裁类,内容主要讲述:第三章:杂项支出里的人心账林夏指尖第二次碰到账本补丁时,没像上次那样慌。台灯没滋啦响,眼前也没发黑,只是眨了下眼的功夫,青石板巷的潮气就漫进了鼻腔——她站在周记布庄门口,竹编柜台后,周明诚正用狼毫笔往账...
第三章:杂项支出里的人心账
林夏指尖第二次碰到账本补丁时,没像上次那样慌。台灯没滋啦响,眼前也没发黑,只是眨了下眼的功夫,青石板巷的潮气就漫进了鼻腔——她站在周记布庄门口,竹编柜台后,周明诚正用狼毫笔往账本上添字,笔尖蘸的墨在阳光下泛着乌亮的光。
“来了?”周明诚头没抬,像早知道她会来。他把一本摊开的账推过来,“你上次说你们那儿算‘管理费用’要记明细,帮我看看这页‘杂项支出’,算不算‘细’?”
林夏凑过去。这页记着:“六月十四日:帮小张买草药,价一角五分(他娘咳嗽);赠李婶粗布半尺(补孙子的单衣);给巷口乞丐两个馒头(今日降温)。”每笔后面都用小字注了缘由,像怕日后忘了似的。她想起自己报表上“员工福利费8620元”那行孤零零的数字,脸又有点热:“比我记的细多了。但……赵老板要是看了,会不会说你乱花钱?”
“他早看过了。”周明诚放下笔,指了指账页边缘一道浅痕,“上周他翻账,看到‘赠布半尺’,把账往柜台上一摔,说‘布庄是做生意的,不是救济院’。”
“那你还记?”
“不记心里不踏实。”周明诚笑了笑,眼角的细纹舒展开,“阿芸以前总说,账是记给自个儿看的。你记清了谁难、谁帮过谁,日子才活得明白。”他顿了顿,又说,“再说,小张娘好了,今早他送了捆新摘的豆角来;李婶补好单衣,带着隔壁王婶来买布——这些,赵老板没看见。”
林夏拿起账页,指尖拂过“两个馒头”那行字。纸页脆薄,却像托着沉甸甸的暖。她在事务所时,老板总说“会计要冷心,数字才准”,可周明诚偏用热乎心记冷数字,反倒让布庄和街坊拧成了绳。
“林夏姑娘?”布庄门口探进个脑袋,是小张。他手里攥着个布包,脸有点红,“周先生,林夏姑娘,我娘让我送点新晒的笋干,谢你们帮着买草药。”
周明诚刚要摆手,林夏先接了过来:“得收。这是***心意,不收她该惦记了。”她转头对周明诚说,“账上也该记一笔——‘收小张笋干一包(谢草药钱)’,算‘杂项收入’,这样赵老板看了,就知道‘支出’换来了‘情分’。”
周明诚眼睛亮了:“还能这么记?”他赶紧拿起笔,在“一角五分草药钱”下面添了行:“收笋干一包,抵情分,未作价。”写完直笑,“你这法子好,既没亏了账,也没亏了人心。”
小张站在旁边听着,挠了挠头:“林夏姑娘懂的真多。我以前总觉得账房先生就会算钱,原来还能这么记。”
林夏心里暖烘烘的。她以前怕算账,怕算错小数点挨骂,现在竟觉得算账是件有意思的事——不是对着Excel敲数字,是把人心一笔笔攒起来,像攒铜钱似的,攒多了,日子就厚实了。
中午帮周明诚核完账,林夏想回现代看看。她摸出账本碰了碰补丁,再睁眼时,出租屋的白墙撞进眼里,桌上的咖啡杯果然还悬在半空,离桌面只差半寸——穿越时的瞬间真的停住了。
手机在桌上震了震,是陈默发来的消息:“林夏,你让查的‘周记布庄’,我找到点东西,老报纸片段,1946年7月的,你瞅瞅。”
附件是张泛黄的报纸照片,字迹模糊,但“周记布庄”“裁账房”几个字看得清。陈默加了句:“报纸说‘周记布庄因账目不清,老板赵拟于七月裁撤账房周明诚’,后面还缺了,我再去档案馆查查。”
林夏的心猛地揪紧。七月裁周明诚?现在是六月中旬,只剩半个月了。她翻出那本账本,想看看有没有相关记录,指尖刚碰到“六月十四日”那页,忽然发现周明诚补记的小字下面,多了行极浅的铅笔印,是她的笔迹——早上在民国帮他记“收笋干一包”时,不小心蹭到了账本,竟连现代的这一本也留下了痕。
这账本真的能跨时空留痕。
她赶紧给陈默回消息:“帮我查查周明诚后来怎么样了?是不是真被裁了?”想了想又加了句,“再帮我问问,周明诚的妻子阿芸,你知道她的事吗?”
陈默回得快:“周明诚的后代周建国,我联系上了,约了明天下午见面。阿芸的事他可能知道,我先问问。”
林夏把账本放进帆布包,刚想换衣服去事务所,手机又响了,是张姐。她心里一紧,以为要问报表的事,接起来却听见张姐笑:“小林,你改的那份报表我看了,‘员工垫付款项对应急病就医’,备注写得好!客户看了说‘你们事务所懂人情’,以后你跟着我做项目吧,别光打杂了。”
林夏愣了愣,才反应过来是自己加了备注的功劳。她想起周明诚说的“账要记清,人心不能算清”,突然笑了:“谢谢张姐,我以后会更注意的。”
挂了电话,她看着桌上的报表,忽然想把“员工福利费”那栏也改改。她拿出笔,在“8620元”后面添了行备注:“含加班晚餐43份(人均200元)、员工生日蛋糕3个(合计620元)”。写完觉得还不够,又画了个小笑脸——像周明诚在账本上画的那个叉,有点傻,却暖。
第二天下午,林夏按周建国给的地址找到老城区。是栋爬满爬山虎的老楼,三楼窗台上摆着盆月季,开得正艳。周建国开了门,手里还拿着本线装书,头发花白,眼神却亮:“你就是林夏吧?陈默跟我说了,你对我爷爷的账本感兴趣。”
屋里摆着个旧木柜,上面放着个相框,框里是个穿长衫的男人,眉眼和周明诚一模一样,只是老了些。“这是我爷爷,周明诚。”周建国指着相框,“他活到92岁,去年才走的。”
林夏松了口气——没被裁,还活了这么久,还好。
“你说你有本爷爷的旧账本?”周建国给她倒了杯茶,“爷爷晚年总说,1946年夏天遇到个姑娘,拿着本和他一模一样的账本,帮他保住了布庄。我们都以为是他老糊涂了,毕竟那时候兵荒马乱的,哪有什么‘跨时空的姑娘’。”他从木柜里拿出个布包,解开,里面是本泛黄的账本,蓝布封皮,内侧有块浅蓝补丁——和林夏手里的那本,连针脚歪扭的弧度都一样。
“这是爷爷留给我的,说‘等遇到懂它的人,再给’。”周建国把账本递给她,“你那本,是不是也有个补丁?”
林夏赶紧掏出自己的账本。两本账本并放在桌上,补丁对着补丁,像一对分开多年的双胞胎。她翻到“六月十四日”那页,周建国的这本上,“收笋干一包”后面多了行周明诚晚年的批注:“此笋干腌了装罐,存了三十年,味仍鲜。林夏姑娘教我记‘情分账’,是真懂账。”
林夏的眼眶有点热。
“你问阿芸奶奶?”周建国叹了口气,“她是爷爷的妻子,1945年冬天走的,病没治好。爷爷说她是苏州人,当年流落到江城,跟爷爷成了亲。她手巧,会绣梅花,爷爷账本上的补丁,都是她缝的。”他指着账本补丁,“你看这针脚,看着歪,其实每针都对着布的纹路,是怕补丁掉了——她总说‘账本要结实,日子才结实’。”
林夏摸着补丁,忽然想起周明诚说“阿芸总说自己不属于这时候”,心里突突跳:“周爷爷,阿芸奶奶……有没有说过什么奇怪的话?或者留下什么特别的东西?”
周建国想了想,从木柜底层拿出个小木盒:“这是阿芸奶奶的遗物,爷爷说她走时交代‘等布庄难了,就打开看看’。但1946年夏天布庄稳住后,爷爷就没动过,说‘等合适的时候’。”
木盒上刻着朵梅花,和账本补丁的绣样一样。林夏打开盒盖,里面铺着块青布,布上绣着枝梅花,花瓣里藏着行小字,是用丝线绣的:“七月望,苏州梅家,持此布可寻亲。”
“苏州梅家?”林夏愣住了——大纲里周明诚后来要找的苏州布商,难道就是阿芸的亲戚?
“爷爷说阿芸奶奶好像姓梅。”周建国补充道,“她还会唱支歌,爷爷记不全,就哼过两句:‘月照青石板,账本落梅花’——你听过吗?”
林夏的心猛地一沉。这两句是她外婆教她的童谣,外婆说“是你外曾祖母教我的,她总说忘了从哪儿听的”。她掏出手机,翻出外婆的照片给周建国看:“周爷爷,你看我外婆,像阿芸奶奶吗?”
周建国眯起眼,凑近看了半天,猛地站起来:“像!眉眼简直一模一样!尤其是这颗痣,阿芸奶奶眼角也有颗!”
林夏攥紧了手心。阿芸是她的外曾祖母!她穿越到民国,竟是回到了外曾祖母生活过的地方。那账本的补丁,哪是什么穿越媒介,是外曾祖母留的绳,一头拴着1946年的周明诚,一头拴着2024年的她。
“林夏姑娘,你怎么了?”周建国见她脸色发白,赶紧递水。
“没事。”林夏深吸一口气,指尖碰了碰木盒里的青布,“周爷爷,1946年七月,周记布庄是不是遇到危机了?我看老报纸说赵老板要裁周明诚爷爷。”
周建国点头:“是有这事。爷爷说那年七月中间商抬价,布庄进不到便宜布,赵老板急得要关店,还怪爷爷‘乱花钱济贫’。后来不知怎么,爷爷突然找到苏州的布商,进价降了两成,布庄才稳住。赵老板不仅没裁他,还让他管进货了。”他笑了笑,“爷爷说,是‘林夏姑娘’教他找的苏州布商——原来真有你。”
林夏看着桌上两本并排的账本,忽然明白周明诚为什么记那么细的账。他记的哪是收支,是想把阿芸留下的暖,一点点攒起来。而她来这儿,也不是偶然——是外曾祖母的梅花布,是周明诚的人情账,早就在时空里搭好了桥。
“周爷爷,我想再去趟民国。”林夏突然说,“我得帮周明诚爷爷找到苏州梅家,也得……问问阿芸奶奶一些事。”
周建国愣了愣,随即笑了:“去吧。爷爷晚年总说‘那姑娘还会回来的’,他在账本最后留了页空白,说‘等她来记最后一笔账’。”
林夏拿起自己的账本,指尖轻轻碰了碰补丁。这次她没慌,甚至有点期待——青石板巷的潮气,周明诚的狼毫笔,还有外曾祖母没说完的话,都在那边等着她呢。
她眨了下眼,出租屋的白墙消失了,竹编柜台的触感又回到手心。周明诚正对着本账发愁,见她来,抬头笑:“你可来了,赵老板刚来过,说要是下周再进不到便宜布,就真要裁我了。”
林夏举起手里的木盒(她竟把木盒也带过来了),晃了晃里面的青布:“周先生,别愁。我们去苏州,找梅家布商。”
周明诚看到青布上的梅花,眼睛猛地亮了——像落了颗星子在里面。